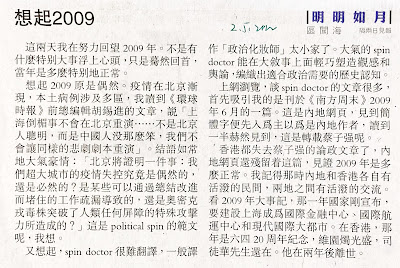這是一個基督教儀式的火化禮和安息禮拜。機構的資深同工、董事、主席、會長幾乎都來了。包括我在內,很多人都比她年長。她的母親的身型和動靜都有些像我的母親。她的疼愛的兒子看來比我的兒子老成。當然也是因為我沒有見過自己的兒子在這樣的深沉哀傷中。
火葬場的儀式規定簡短,也不能早點進場,大家都在外面安靜等候。這天在兩天大雨之後,陽光初現,有雲,禮堂在一個高位的平台上,平台有兩個安靜的睡蓮池,在初夏只有稀疏幾盞浮在如鏡的水面。她的遺照由兒子雙手捧在身前,溫和的陽光散落她的臉上,並不反光因而異常鮮明。她的眼神和微笑的堅定面容都煥發光亮。不知是誰在身邊輕聲說:「她工作中就是這個樣子。」
她是一個真誠、勤勞、獻身服務的社會工作者,從前線到管理行政到領導機構,始終如一地胼手胝足,完全專注於做好給長者的服務。她的完全投入起先讓我懷疑是不是有點完美主義的性格,但認識之後,就知道不是。那是她真心著緊。因為這個著緊,她一直努力推動機構服務在很不容易的環境下持續改進和更新。然後,就在退休年齡漸近時得了病。於是我又見到她堅強面對惡疾的一面。
在艱難的療程中她依然捨不得熱愛的工作。無論如何,上天,她虔信的主,只讓她獻身長者服務到這一點。從此安老服務少一人。在一張藍色的心型貼紙,我寫上「安息 懷念 謝謝你」,與一枝康乃馨同放在靈柩上。
《明報》副刊「明明如月」專欄,23/5/2022刊出。